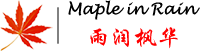在有关北大教改的讨论中,学术自由、学校的官本位和学术规范是经常被提及的问题。一些对北大教改方案持批评态度的学者强调,大学改革最重要的是推进学术自由,破除官本位,建立学术规范。但在我看来,这些批评者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们所主张的这些东西也正是这次改革的目的所在,也只有通过这样的改革,才会有真正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才能真正打破官本位。
学术自由
对于一个大学或者任何一个以创造知识为目的的组织来说,学术自由都是非常重要的,伟大的思想无不来源于自由的探索。这个道理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大家就都明白。但是学术自由并非一般人理解的那么简单。中国大学教师过去都是“铁饭碗”,应该说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但有学术自由吗?很显然没有。大家这么强调学术自由,无非是感到学术不自由,或者学术自由事实上受到了威胁。那么我们就该想想,这是为什么?从大的方面,跟宏观制度环境肯定是有关系的,就是说学术自由可能来自政府对于学术自由的限制,可能来自学校行政当局的限制,以及目前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某些限制等。但是一般人可能忽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学术自由的限制也可能来自教授队伍自身。
很多人会对此很惊讶,但事实如此。洪堡曾说过这样的话:“学术自由不仅会受到政府的威胁,还会受到学术组织本身的威胁,这些组织一开始有一种特定的观点,然后就倾向于压制其他观点的兴起。”对科学创造最大的阻碍常常来自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学者,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已经有了自己的学术框架,容不得新的思想出现,任何新的思想都被看成是对他的学术权威的挑战。这在全国许多科研机构都是这样,在“家族制”普遍的高校尤其如此。
在我们现有的制度下,即使没有政府的限制、没有学校当局的限制,也还有“家长”的限制。你想想,在婆婆面前,你老是个小媳妇,你能自由地思想和进行学术研究吗?自由创造的前提是自由思想。当你在你的老师面前,想提出一个跟老师不一样的观点的时候,你预期将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他十有八九会不喜欢你,极端的时候甚至可能限制你,或跟你闹翻了。中国高校目前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很大一块是来自这个。这也是我们必须破除“近亲繁殖”的原因之一,因为在“近亲繁殖”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有些人很热衷于谈学术自由,但又反对不留自己的毕业生的改革,这是自相矛盾的。
哈佛大学前校长陆登庭说过这样一段话“: 除非大多数年轻教师在试用期内就离开学校到其他地方去谋职,允许学校每年都不断地聘用新的年轻教师,这些人把他们的新思想和他们受到的最新培训带到学校来,否则学校就会很快变得停滞不前。理想的状况是学校各级人员不断更新,在许多领域知识变化迅速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重要。”
就是说,学术思想只有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下,才可能有自由。看看中国人文历史,都是人才出现流动以后,学术思想创造才会出现。这就像有出息的孩子都是离开父母之后,才变得有出息一样。父母在的时候孩子始终是长不大的。
如果有些人把学术自由理解成喊政治口号,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我的经历以及我这些年的观察使我相信目前外界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可能小于学校体制内部本身对你的限制。尽管存在一些禁区,但仍然有许多非禁区,是我们自己束缚自己拿不出研究成果来。经济学领域就是这样。当然,终身教职对从制度上保证学术自由也是很重要的。当你拿到Tenure,如果你没有明显的道德过错,任何学校当局都不能因为不同意你的观点而解雇你,从行政方面讲,校长没有权利开除一个因为观点跟你相左或者是你不喜欢的人,这样你才有学术自由。但我们绝不应把终身教职与过去的“铁饭碗”相混淆。这个制度的目的,首先在于选择最优秀的老师队伍,而过去的“铁饭碗”与此背道而驰。
学术自由也与学者本人的学术水平有关。追求学术自由是智者的天性,而“政治上正确”是庸才最好的保护伞。中国有句古话“艺高人胆大”,就是说只有武艺高的人胆子才会大;武艺不高,胆子就大不起来。
我们都知道北大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是一个非常敢讲真话的学者,为什么?因为他水平高。如果我们有一半的教授能达到类似钱理群这样的水平,你要让他不自由也不可能。水平不高的人不仅自己胆子小,而且往往喜欢给别人扣政治帽子,用不正当的手段与人竞争。所以,有利于提高教授学术水平的制度客观上都有利于学术自由。
当然,我们不能把“学术自由”理解成学者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任何行业都有行规,学术自由不是说老师想开什么课就开什么课。全世界没有一个大学说老师想开什么课就开什么课。美国的大学许多课程编号甚至几十年不变。你要开新的课得要有一个程序,这个课要经过一个委员会(faculty)的讨论,系主任的批准,你才能开。因为你必须对得起学生,而不是自我欣赏,自己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学术自由也不能违反学术的基本规范。好比说,人家都讲1+1=2,你说我要自由,非要1+1=3。这不能叫自由。如果一个学者不承认大家认可的基本的研究方法和规范,这样的“学术自由”便是伪学术自由,是对学术自由的滥用。
学术自由与大学的逻辑是相一致的,是为了创造知识,为社会创造价值,而不是为自由而自由,学校也不能追求自由最大化,而应该追求创造知识、为社会贡献最大化。我们为什么强调教授要有更多的自由,这个自由比一般的行政机关要大得多?教授一般上下班都比较自由,行政官员、国家干部上下班能自由吗?那不行。给教授自由,不是因为教授学历高、知识水平高,就可以搞特殊,而是考虑到知识生产的特殊性,教授自由上下班更有助于他的学术成就,也就是说,自由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大学的逻辑,完成大学的理想。
“官本位”
中国历史上长期只有一个Hierarchy(官僚等级)的激励制度,官位成了惟一度量个人成就的标准。在中国的大学里,行政本位、官本位相当严重,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分房子、发工资,什么待遇都是按照行政级别来划分的。不打破官本位,要建设一流大学是不可能的。
问题是,为什么官本位这么严重?在我看来,学校的官本位,除了传统思想和激励制度的扭曲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是内生的,与学术规范有关,与学者水平有关。
在中国学术界,因为缺乏好的学科规范,学术成就不能有效比较,学者之间就不可能相互欣赏。这样一来,做学术的人常常会感到很无聊。到头来评价一个人是否优秀的标准只能寻求学术之外的标准。毕竟,人家官本位还有一个序列,还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可比较,而学术却没有标准,那就只能套官本位来比较了。
在高校,什么样的人最重视当官?什么样的人官本位的观念最强?一般来说是学术水平低的人,官本位思想越严重。反过来,高水平的学者通常很自信,很欣赏自己创造的成就,对当官的反而不太容易看得上,更喜欢以自己的创造,自己的学术成就来衡量自己的地位。在一个系或一个学院中,真正高水平的教授,他还会在乎当什么系主任、院长吗?像北大的季羡林教授,他才不在乎当什么官呢!在美国的优秀大学,院系行政职务常常要靠轮流,因为谁都不想干那个活。那是服务别人的事,伺候别人的事,还影响学术研究,没人愿干。而低水平的教授则不同,他在学术上竞争不过别人,就拼命找一些其他的关系来压制别人,如靠行政级别来提高知名度。如果大家水平都低,社会上就只能根据职位来推定学术水平,大家就会拼命去争行政职务,这样一来更没有人热心搞学问了。
中国大学的好多教授喜欢“占摊儿”,所以大学里各种研究中心、研究所林立,但很少有作出出类拔萃的研究成就的。其实这部分地反映教师队伍学术水平低的状况,没有研究成就奉献社会,就只能用头衔闯江湖。
我做过一些研究,发现几乎任何组织都是这样:一个组织越是水平低的人多,就越是着迷于内部权力斗争。水平高的人忙着去创造价值,水平低的人忙着去分配。高校的官本位只能把大家的精力引向分配,而不是创造价值。
因此,破除中国大学的官本位,必须回归到大学的逻辑,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提高教授的水准,而这正是北大改革的目的。相信北大的这次改革对冲破官本位是非常有益的。比如说,不直接从本院系招聘应届毕业生当教员,就会对官本位产生很大的冲击。在现在的体制下,导师的官越大,学生留校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最容易招到学生的一定是有官位的人,而不一定是学术水平最高的普通教授。这样,就激励教授当官。在新的体制下,比如说,当有十个外校的博士竞争一个本校职位的时候,学术标准,而不是导师的行政职务,就会成为学校聘任的主要标准,一个人要找到好学校,就要有真才实学,就要跟真正有水平的教授,而不是当官的教授。这就会大大降低教授当官的积极性。
学术规范
提高教授专业水平,并且建立起学术自由风气,当然离不开学术规范、专业标准。改革的过程也就是学术标准的建立过程,因为学术标准是内生的。学者的学术水平不高,就不会有什么像样的专业标准。学术标准一定是高水平的伟大的学者建立起来的,在街上随便找个人来建立学术标准是不可能的。要是大学中低水平的人多了,一定不会有真正的学术规范。中国的人文科学可以说普遍存在这个问题,社会科学也很严重,没有办法进行比较,自己拿不出学术规范,所以只能挂靠行政评比。
评价学术成就和评价普通产品是不一样的。一个市场上产品的评价最终是消费者作出的。你不能让几个电视机厂家凑到一起评谁的电视机最好,这没有意义。但是学术的标准、学者的标准要学者自己评价,即同行评议。
为什么是同行评议?是因为知识产品的特殊性。教授们在大学里生产的知识和思想尽管对人类长期发展很重要,但在短期不一定看出效果来,没有办法定价。许多学术研究当初并没有看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后来发现价值很大。类似这样的研究在市场上是没有办法显示出价值的,只有同行才有可能作出评判。我们也不能指望让学生去评价老师是不是优秀的教授,学生最多只能评价老师是不是一个讲课优秀的老师,没有办法评价优秀的研究型教授,因为学生的知识也有限,他本身还在学习,所以由同行来评价才是最优的选择。如果整个专业有一百个教授,就由这一百个教授说谁是最好的,才有意义。
那么这时候问题就在于如何设计一个制度,让这一百个教授能说真话,真正评出大家都认同的最好的学术研究来?由此就引出学者的学术规范、学术训练问题来,这些问题对于学术评价非常重要,当然前面讲的学术自由也很重要。
从学术的行政管理角度来讲,最重要的是尽量做到程序公正,以此保证最终评价的公正,但没有办法提出具体的要求,好比规定发表几篇文章就够教授等等,这只能由教授们自己去评价。程序公正,是为了防止内部人操纵,因为难免存在裙带关系或情面的问题。所以全世界学术评价还有一个重要规范就是引入外部人评价。说你是一个优秀的教授,不能由系里的几个教授说了算。因为学术的标准是统一的,我们要看外部的教授怎么说你,所以引入外部评价机制非常重要。这也是北大改革方案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改革到位后,今后谁能当北大教授,不是北大教授说了算,还要听外部同行说。这个“外部”包括北大校外甚至国外。在我看来,有条件的大学应该扩大范围,多邀请一些国外的教授来评价。
我再三强调,学术领域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统一的标准。这跟做企业还不一样,做企业就是我这企业有我的文化,而学术标准一定是有共性的。你自认为是一个好的教授,结果国内外同行都不认你,那肯定不行。但是在中国,由于这么多年破坏了学术规范,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几乎完全谈不上学术规范。有人建议说中国要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院士,我看实在是不好选,因为没有一个规范、没有一个标准,你怎么选?学术标准不是说大家吵吵嚷嚷,提出一个口号就能建立的,只能是通过不断提高教师的水准,不断引进外部评价机制才有可能建立。
有人可能不相信,认为选择好某些“科学”的指标就可以了,其实任何硬性指标规定都会导致扭曲。试想,学术委员会的委员,他本身的学术水平只是三流,他怎么来评价一流水平的教授?还有人经常自称某某研究填补了国家空白,有什么重大创造等等。他自己能评价这个吗?不能!所以学术标准是内生的,我们只能保证程序上做到公开、透明,引入外部竞争,来保证尽量做到一个好的学术标准的树立。但不要期待一天就做到建立硬性的学术标准。
另外,每个学科的学术标准都不一样。比如说,有的理工科教授发表的文章特别多,他任何一个小实验都可以写一个文章去发表。在美国,一个高产教授一年在SCI上的文章可能有几十篇,他带领一大帮人去做这个研究。但是,文科显然不可能。那么,到底几篇文章够教授,什么样的杂志为够,你肯定不能硬性规定,只能靠本学科自己来定。这就像有的地种土豆,有的地种芝麻,不可以亩产论高低。
北大的改革目标之一,就是希望以后按照学术贡献和学术水平评教授而不是按照发表的论文数量来评。所规定的标准只是抽象的,如你必须在本领域达到最优秀的层次,并没有规定你发表几篇论文。但接下来各个院系肯定会增加一些数量方面的要求。为什么还要增加具体的规定?这就又回到前面讲的,如果你没有定下具体的标准的话,操作起来会造成困难,容易产生学术腐败。
我常想,一流的大学看质量,三流的大学看数量。北大现在还不是世界一流,但北大想成为一流,所以我们既看数量又看质量。当我们已经达到一个程度,使得我们不看数量就可以选出最好的教授的时候,我们绝对已经成为世界一流。张五常写文章说,他曾问在芝加哥大学当经济学教授要发表几篇文章?回答是“没要求”!不写文章行不行?也可以!但你要说话,让人家服气,知道你有思想。达到了那个境界了,那就是真正的一流大学。北大现在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因此还必须从建立硬的标准,保证优秀教授的筛选入手,也算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吧。